舒兰市人民政府网站欢迎您的访问!
05-08 星期四

舒兰市人民政府|
2014-06-20 11:15|
信息来源:舒兰市人民政府
理想与责任,执着的坚守——记吉林市2013年度“最美教师”张孝东
“老师,您现在身体怎么样啊?工作还顺利吧……”电话里传来深情的问候,手握电话的老张,嘴里不住的说着:“都好,你也一切都好吧……”老张叫张孝东,今年52岁,是吉舒街中心小学大北村小的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给他打电话的是早已毕业,目前是天津一家公司的老总徐晓敏。每逢年节,她总要给老张送上问候、捎来礼品。
笑对磨难 站在与命运抗争的第一线
一个人的脊梁所能承受的极限,到底能担负起多少生活的重压?幼年患病,是否会带来一生的阴影?童年丧母,是否会影响一个人的心智?中年丧妻,是否会让人一蹶不振?如果——仅仅是如果——上述的某一项厄运不幸地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是否还能面带微笑、挺起脊梁?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答案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犹豫。可老张,一个其貌不扬、年过半百的山里人,一个名声不显、身有残疾的普通乡村教师,却经受住了生活于他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用豁达的心态去面对命运的捉弄,用孱弱的身体站成了一个大大的“人”字,而且在许多方面都站在了身强体健的普通人前面。
老张话语不多,朴实充盈其间。然而命运的捉弄却使他拥有了不普通的生活经历:3岁时一场不被人重视的感冒,不想却是脊髓灰质炎的前兆,病愈后他终生都只能拖着左腿前行。11岁时,疼爱他的母亲又过早地辞世,留给他的只有忙于生计的父亲和需要照顾的幼弟。生活的磨难使得老张在小小年纪就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成熟。当别的孩子还躲在被窝里睡懒觉时,他却要早早地起床为家人张罗早饭;当别的孩子在父母的照顾下衣来伸手时,他却要代替母亲操持起所有的家务;当别的孩子放学后嬉戏玩耍时,他却趴在炕头预习第二天的功课……似乎是皇天不负苦心人,从小学到初中他的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在那个小学毕业就是“文化人”的年代里,他这个初中毕业生成了村里远近闻名的“大学生”。但命运之神又一次打破了他对未来的憧憬,1980年,就在他即将升入高中期待用知识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干了20多年民办教师的老父亲却因为教学点的撤并而不得不离开钟爱的教育事业。没了收入自然也就支撑不起老张的求学梦,19岁的老张就这样草草地结束了学业,成为了不能从事劳作的青年农民。没有书读、没有工做,只能窝在家里,命运的不公激起了老张不服输的劲头。不能下地,他便在家里操持家务,将两间草房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能耕种,他便搞起了养殖,养鸡养鸭倒也让小日子过得衣食无忧,可这并不是老张想要的生活。1985年,因学校急需教师,他这个村里的最高学历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当年3月份他成为了大北村小的民办教师。虽说一年只有504元的补助,还不如在家里养鸡养鸭赚得多,可老张就是喜欢这种氛围,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能让我的书白念了,更不能让孩子们没有书念。
虽然老张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可当时这个舞台所赋予他的价值却无法让他有一个安稳的家。直到90年代初,老张才盖起了两间砖瓦结构的厢房,老张还是守着父亲过日子。但老张不气馁也不抱怨,每当有人问起婚姻问题时,他总是豁达地说:“这样挺好,没有妻子的牵扯,我能更精心地伺候老人;没有家庭的负担,我能更好地照顾学生。再说我这身体条件怎么好意思去拖累别人。”直到1996年,一个比老张更需要照顾的人让老张动心了。经人介绍,老张认识了邻村的刘丽杰。这是一个比老张还要命苦的女人,身体虽完好无缺可却患有癫痫病,每天都离不开药物的支持,让家里人苦不堪言、难负其重。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老张接纳了刘丽杰,想用自己的力量为这个同病相怜的女人撑起一片天。同年,老张终于有一个完整的家——尽管这个家在外人看来带给老张的更多的是一种负累:老父亲年迈体弱,根本无法从事耕作,病妻子常年用药,只能操持简单的家务。可对老张而言这个家带给他的是一份牵挂、一份责任:成了家,他的生活格外的忙碌。每天早晨,他早早起床,做出一天的饭菜才急匆匆地赶往学校,每天中午还要挤时间回家,看看家中的老父病妻,喂喂家里养的鸡鸭;成了家,他的日子格外地清苦,老父的胃口再刁他也会精心调理,妻子的药再贵他也买得毫不犹豫,可却偏偏舍不得自己多花一分钱,为了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他竟一下子就戒掉了吸了十四年的烟。2009年,老张用多年的积蓄盖起了村里最漂亮的大房子,终于用自己的行动兑现了他对家人的承诺,可相濡以沫的妻子却没能陪他一起去迎接更美好的未来,2011年12月,妻子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不幸离世。家里一下子塌了半边天,老张一整个冬天都闭门不出,就在大家都苦于无法劝慰老张时,他却在开学的第一天准时地来到学校,大家熟悉的那个坚强、乐观的老张又回来了。
“日子总得往前看,老父亲还需要我奉养,孩子们还需要我教导,就是丽杰也不会希望看到我倒下去。老天爷想让我低头,我偏要站直了给他看。”说这话时,老张的腰板格外的挺直。
笑面学生 站上教书育人的快车道
如果说对家人的付出源自于牵挂和责任,那么老张对学生的关爱则更多地源自于一份热忱与一份憧憬。回想起到学校上班的第一天,虽时隔多年老张却依然难以平静:“一进学校,感觉自己的病腿都不那么沉了,尤其是站在讲台上,能够完成父亲未竞的心愿,能够实现自己儿时的夙愿,真是想想都来劲儿。”可老张没想到的是,学生和家长对他却不怎么“来劲儿”,家长们对他能否当好老师普遍都表示怀疑:一个残废也能教课;孩子们的表达则更为直接,背地里都叫他“张瘸子”。对此老张却不以为然,他选择了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对于孩子们的耻笑,他的回应是:“人靠两条腿来支撑,一条腿是身体素质,另一条腿是知识能力,老师的知识太过突出,身体素质跟不上就成了张瘸子,你们每个人都有着让我羡慕的健康的身体,可你们的知识能力能跟上吗?你们也想和老师一样做一个身体和知识不匹配的瘸子吗?” 短短的一席话,语重心长又不失风趣幽默,迅速地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而他同样精彩的课堂教学也让孩子们如痴如醉,钦佩他渊博的学识而有意识地忽略了他身体的残疾。一个学期下来,他教的学生不仅成绩显著提升,就连行为习惯与内在气质都与其他的山里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下子就让那些曾经议论纷纷的家长们没了话题。
老张这辈子有两大憾事,一是由于妻子身染重疾,他终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二是因贫辍学的他总觉得自己的书读得太少。让人欣慰的是,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这两大憾事都得到了弥补,他把每一个学生都视如已出,他教过的孩子没一个中途辍学。为了让悲剧不在孩子们的身上重演,老张可真是没少费心:为了让孩子们学习有兴趣,他把每一节课都当作公开课一样精心准备,妙语连珠、由浅入深,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课堂上找到乐趣;为了孩子们读书有动力,他经常用自己的工资买一些小礼物,当作对优秀学生或学习进步学生的奖励,让每一个孩子都卯足了劲儿地学习。可山里的风气却不是一个人短时间内就能改变的,老张班里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也经常因为种种不称其为理由的理由而面临辍学的威胁,为此老张常常用自己的工资为孩子贴学费、补学习用品。1990年,老张带的毕业班有一个叫徐晓敏的孩子,在秋收假后突然就不来了,老张去家访,家长直接告诉他:地多人少,忙不过来,女孩念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最后也是赔了自家的钱贴补别人,还不如帮家里多干些活呢。老张苦口婆心地反复劝说也不见成效,最初徐家人还有一分客气,最后干脆来了一个避而不见,实在躲不开的时候就说一些比较伤人的话。对此老张一点也不生气,也不再劝说家长,而是每天下班急忙回家做饭,然后就跑到徐家的玉米地里跟着割玉米,一句话也不多说,干完了骑上车子就回家。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义务工一干就是一个礼拜,看着老张拖着病腿埋头苦干,徐家人几次凑上来讪讪地想说些什么却最终也没张开嘴。收完了玉米,没用再做工作,徐晓敏就回到了学校。现在的徐晓敏已经是天津一家公司的老总,全家人也跟着进了城。可每逢年节,她总要给老张送上问候、捎来礼品。2013年年末,徐晓敏联系天津市海河文化发展基金会为大北小学捐助5000元钱为每名在校学生购买了羽绒服。一次电话里徐晓敏动情地说:“老师,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的命运是您改变的。”老张却毫不居功:“应该说是知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用知识改变山里孩子的命运,这就是老张能在孩子与村民面前挺直腰板的底气。
“1993年的一天,我收到了来自山东泰山医学院的一封信。这是我教过的学生李志清考上大学的来信,她是要跟我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老张边说边回忆着。李志清是老张1984年所教毕业班的一名学生。老张在教学时不仅努力提高学生成绩,同时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鼓励学生刻苦学习,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奋斗。当时,李志清毕业后就随家人回到了山东,临走前夕,李志清找老张谈心:“老师,你说我能考上大学吗?”这是多么好的志向啊,老张当时就说:“当然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你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加油吧,你一定行的!”李志清听后非常高兴:“老师,谢谢您。谢谢您教我!”“如今,李志清如愿考上了大学,看着孩子们成长了,付出多少都值了!”三尺讲台,一颗爱心,放飞了希望,却乐此不疲。老张憨憨地笑着。
笑看荣辱 站在舍已为公的最前线
顺境逆境看胸怀,大事小事看担当。活了大半辈子的老张对家庭有担当 、对事业有热忱、对学生有爱心,无论是亲人、同事、学生还是村民,提起老张没有不竖大拇哥的。“2013年夏天涨水,从我们屯到学校有段路被水淹了,约有一个4、5米宽,1、2米深的水坑。为了方便外出,村民们在上边横一根木头。那段时间里,张老师为了不耽误给学生上课,是爬过去上班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冬天雪大,他也是边走边扫条道去上班的,这才是人民教师啊!”邻居隋建龙感慨地说。
按说老张也该是大北乡数得上数的知名人物了,可偏偏工作了30多年老张就是名声不显,评职称时数来数去也就10多个证书上,还都是学校内部的教学奖励,政府颁发的奖励只有1993年的舒兰市优秀教师和两次被评为二道乡优秀教师,就连入党也是当了十三年积极分子才转正。不熟悉内情的人往往会误以为老张是徒有虚名,可同事们却忍不住为老张正名:不是老张不够格,而是老张发扬风格。每次评先进老张都排在前面,可他却总是要求把自己排在后面。朋友们总说他傻,哪有到手的荣誉往出推的,可老张却振振有词:“政府和学校对我照顾得够多了,逢年过节我们中心校的校长都来看望我,就连政府的书记和乡长都来给我过教师节,可我能做得却太少了,有了荣誉咋好意思再往前冲?再说其他的老师和老乡平时对我也没少照顾,我咋能和他们争荣誉?”听了老张的这番话,朋友们虽心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慢慢地熟悉了老张的脾气也懒得怪他,而老张也乐得清静,继续做他的“张傻子”。
“张傻子”其实一点也不傻,作为民办教师的他早早地就考上了师范,转了正。1999年的时候还凭借自己的努力参加了成人高考,在工作之余刻苦自学,没费多大力气就顺利地获得了大专学历,让大家对他又是刮目相看,都以为这“张傻子”终于开窍了,可没成想一转身老张又干了“傻事”。2005年,胜和村小因教师退休而严重缺编,但中心校却迟迟调不过去人手,问题只有一个:路太远——作为吉舒街中心校最偏远的一所村小,胜和学校离吉舒镇足有70多里路,相邻的村子最近的距离也有30多里。为了调派人手,当时的中心校领导可没少费心,可就是没人肯去,正当中心校领导犯难的时候,思虑再三的老张主动报名了。老张的报名不仅让同事们意外,就连中心校领导也是左右为难,不派他去——胜和学校的教育教学就无法继续;派他去——又担心他的身体和家人。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中心校领导做起了老张的工作:“孝东,你去支教,身体能撑得住吗?胜和学校离你家三十多里,路又不好,你的家人你能顾得过来吗?你,还是别去了。人的问题我们再想办法。”可老张却异常坚决:“困难谁家都有,我犯难别的老师就不难吗?我是一名党员,关键时刻我怎么能落后?领导和同事一直都对我关照有加,有困难的时候我怎么能往后退?至于家里人,我已经跟家人说好了,大不了我早点起来做饭。关于我的身体更不用领导惦记,除了一条腿不行,其他的零件都结实着呢。”看着老张诚挚的眼神,听着老张朴素的话语,再多的劝阻都显得那么无力。老张不仅话喊得响亮,事也做得漂亮。每天早晨都是老张最忙的时候,天刚透亮老张就起来张罗早饭、收拾屋子、操持家务,然后又急急忙忙地往学校赶,生怕迟到一分钟;每个冬季都是老张最难的时候,冒着刺骨的寒风,走着或光滑、或积雪的路面,三十多里路对于老张而言常常是跌倒爬起的循环往复。可老张硬是坚持了三年,直到有新教师到岗才又回到大北村小。
本以为回到原单位的老张能干得轻松些,没成想他承担的工作任务比以前更繁重了,而且还都是他主动要求加的担子。班主任是他的老本行,再加上经验丰富,带个毕业班终归是无可厚非——交给别人领导也不放心。可他偏要主动请缨兼任学校的少先队辅导员等工作,理由竟是不多做些工作他不安心。工作任务虽繁重,可老张却干得有滋有味。在学校,老张忙得没有一点闲暇时间,每到课间都到操场上巡视,每天放学也是他组织站放学队;在家里, 老张也没有多少私人的空间,操持完家务的他不是谋划着新的活动安排,就是整理归档各项活动材料以作为下一步工作的借鉴。
看到老张遇事往前冲、重担抢着挑的“傻样”,朋友们都想不通,想不通年过半百的老张干工作还这么拼命到底是图个啥?可老张却说:“我是老师,就应该站在需要我的讲台上!我是党员,就应该冲锋在前!我已经年过五十,蜡头不高喽,再不多干点活儿以后还能有机会了吗?”与老张同行,很多人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公私难以兼顾的时候都会习惯性地抬起头、向前看——因为老张就站在前面。(于晓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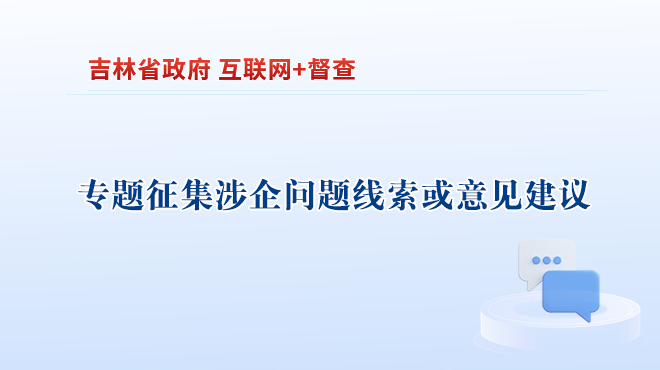













 吉公网安备 22028302000102号
吉公网安备 22028302000102号




 首页
首页



 舒兰市人民政府
舒兰市人民政府